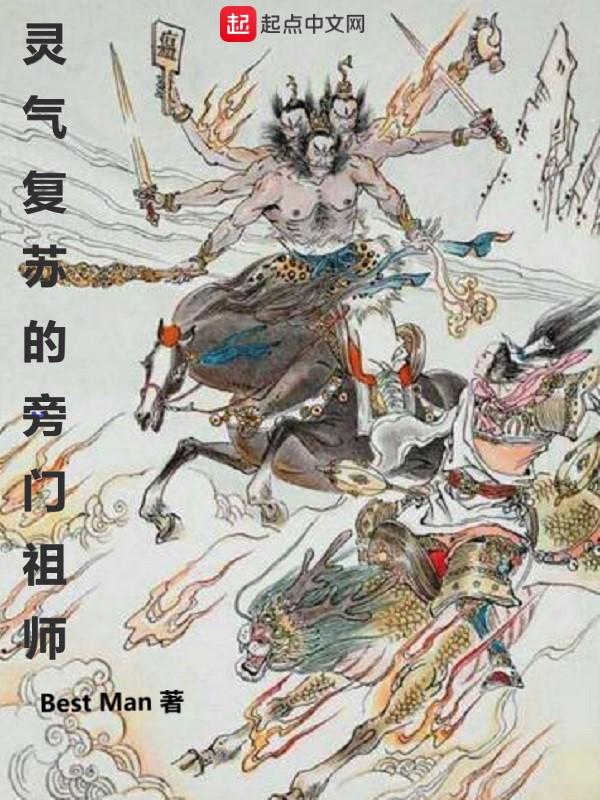悠哉小说网>荆棘吻 > 第99章(第1页)
第99章(第1页)
谈铮拿着病历本坐在一旁,欲言又止。
他明白,所谓的“家属”,多半是医生的顺嘴一说,未必就是真的把他当家属。但看见祁纫夏满脸着急解释的模样,他斟酌几秒,还是不失风度地问了句:“要我帮忙澄清吗?”
不知怎的,祁纫夏听出些许揶揄的意思,心下不爽,索性把眼睛一闭,开始凝神静气。
“放心,我没那么小题大做。”她说。
谈铮不觉弯了唇。
他静静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垂眼看着闭目养神的祁纫夏。
她手臂和头顶的不同穴位都扎了针,乍眼瞧起来,倒是像一只睡着的刺猬。
只是刺猬的刺朝外生长,她身上的针,针尖却朝里。
不同的诊疗床之间,有蓝色的帘子阻隔,祁纫夏躺在最角落,墙角和遮光帘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狭小空间,像小时候喜欢用靠垫和枕头垒建的安全屋,遵从生物本能地寻求庇护。
谈铮轻微地恍神,似乎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里,找到了一丝绝不该出现于此的静谧和安宁。
过去的这段时日,他常常思考,自己现在和祁纫夏究竟算是什么相处模式——分明已经逾越了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界线,其中掺杂的感情成份却实在存疑。
唯独最近似乎终于出现了向好的趋势,祁纫夏好像不怎么排斥和他的亲密行径。
也许是身体记忆。
他徒劳地宽慰自己,这起码总比保持距离来得好,至少,他还有可以留在她身边的机会。
“夏夏……”
谈铮情难自抑,低低叫她的名字。
祁纫夏眉心动了动,却未曾睁眼。
她此刻正处在半梦半醒的混沌里,难得在白日打起盹来。冥冥之中,她隐约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叫自己,可是侧耳再听,却又消失不见。
大概是幻听。
她迷迷糊糊地想。
*
医生来拔针时,祁纫夏才刚刚清醒。
“我是不是睡着了?”
体感和现实偶尔存在落差,她没留神时间过去多久,便只能问谈铮。
“是睡了一会儿,我叫你,你没反应。”
祁纫夏神色有些不自然,讪讪道:“怎么不直接叫醒我。”
谈铮:“你已经失眠到了需要看医生的程度,如果我还要在你睡着的时候把你喊醒,也太没有人性了。”
说话间,老中医走过来,缓缓为祁纫夏拔下身上的银针。